新河头陈浩盐水鹅:传承百年的水乡美食

照片:如悦
一
白马湖东北岸的南门已经优化成漕云镇,但新河头市场还在,新河头集镇有多古老,它应该像新河一样经历数百个春秋两季,这里是白马湖水乡的精神,是处处水文化的特色。
一位作家对这里的饮食文化很感兴趣,曾经在新河头住了几天,说这条小街上的几家小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,而且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水乡风味。其中,特别提到了陈浩家楼的咸水鹅,说别的地方吃不上。
要说陈浩酒店对我来说很熟悉,尤其是酒店的老板陈浩说,他和我的同学,而我是村民,和我同龄,童年伴随着学校的启蒙,记得他是文盲,活泼调皮,那时候他和我就被称作石矿, 大概在二年级,他复读了一遍,到了下一堂课。我小学没毕业,后来就进了部队两年,改革开放后开了一家小餐馆。
我听说在他眼里,我只是一个臭文人,有时候别人请我去他家吃饭,我走的时候,他还说了一句烦人的话,今天哪家歪了,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正视我,大概是因为我穷。是的,他当时很愿意,能够经常请重要官员吃饭,主要是为了打理他的生意,在缴纳工商税和安检时给予优惠待遇。记得年底的时候,他带着一大批发票到镇上找领导审批。
那一年,他的店里写了个牌子,叫姐夫来找我,他姐夫是我的高尔夫球手,我们南门已经很多年了。我当时觉得很奇怪,你陈浩没认出我来,怎么不能装个面子。
要说陈浩真的是一个绝对精明的商人,他在新河头街打造了“老陈老鹅”的食品品牌,生意还真是蒸蒸日上。影响到远近的城镇和村庄,他每天可以卖出几十斤的咸水鹅,甚至城里的几家餐馆都买他的鹅来装饰门面。既然你出名了,我这个作家就想关注他,尤其是这些年来在食品界倡导的非遗品牌,我找到了他,他还是上下直言,说:“我看不懂,不要那个恶名,如果你真的想写,可以帮我报道, 如果你想用竹竿敲我,你可以说清楚。“天哪,你见到他,这个不讲道理的人还真叫'秀才遇见一个士兵,他讲道理就解释不了'。
前几天,白马湖办公室的老板提出要推广新河头饮食文化品牌,今天早上九点就去他家门口面试。他似乎还是不太热情,我告诉他我要做什么,但他没有回答,说:“很简单,我不能告诉你,所以请帮我旋转一下。随心所欲地写。“我说我真的要打你一巴掌,然后找到你家庭的阴暗面,把你捅进社会,还让你没有好名声。”他听到我说这句话,有点严肃,“我们都是老兄弟了,你真想让我好看,我还打不过你。原来他也有点害怕。

第二
。二、二
这时他有些严肃,特意从吧台里拿出一把软椅让我坐下,说:“哥哥今天在这里吃饭,平时不请你。”
他很认真的说道:“这咸水鹅手艺,已经传了三代了,至于朝廷,也不知道能传出多少代。你知道我是文盲,我父亲恨我不识字,但不会钢铁。当有人问我以后会做什么时,我说:“等我长大了,只要我每天都有肉吃,我就会像你一样开一家餐馆。在青年的饥荒年代,哪个人不饿。没想到打歪了,还真用上了父亲传下来的手艺。”

陈浩的父亲名叫陈大红,因为红锅,被别人叫了一辈子。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陈浩父的父亲,他叫陈兆鹏,早年是当地有名的红锅师傅,不知是不是老太太传下来的。那时候,老家穷得厉害,老太太(这是陈浩叫他的儿子)十八岁带着老家的一群人去江南裕廊山做苦力,老太太很勤奋,有一天农民工食堂加菜,那是从附近买来一只老鹅, 到食堂红烧,厨子的嫂子没有包鹅毛、烤鹅的能力,当时就让陈兆鹏帮忙。
谁知陈昭鹏还真懂得烤鹅的诀窍,缠上鹅毛也就行了。附近有一家中药店,他买了一些四川花椒八角,先煮了一锅盐开水,当时是大珠子的盐,说冷盐开水不仅能析出水的杂质,而且盐味能均匀地渗透到鹅肉里。还有白酱油、大豆油、葱、蒜、姜、茶、白酒。这时,我从很远的地方闻到了香味,味道很好。他还用一个小盆把鹅汤放了上来,说下次他煮的时候,老鹅肉会更好吃。就这样,他因烤鹅的本事而声名鹊起,大家一致要求他当厨师,这样他就不再在工地上当苦力了。那时候,普通人很少吃鹅,裕廊街上一家酒馆的老板知道后,特意花钱请他当酒楼里的红锅哥。
就这样,陈昭鹏在江南句容几年后回来了,因为家里有老婆孩子,在当地大街上开了一家小餐馆。
三
大概早些年,陈兆鹏常年不在家,孩子不多,生活负担也不重,家里土地虽少,但小日子还是比一般贫苦农民富裕了许多。陈兆鹏心机十足,以为工匠不会饿死在饥荒中,于是就教了儿子陈大红一套红锅功法。
老一辈的农村男孩很少识字,原因是当年没有中文学校,经常有大方的私塾礼堂,私塾礼堂的绅士去学生家发饭,教室只在农家。
陈大红成年后跟着父亲学会了红锅做饭的手艺,酒楼也没办法了,只是为了帮附近的大户人家做喜事,有几桌菜请他到车站厨房,他做的菜很有名,但烧老鹅的人却很少, 也就是说,八个碗之类的。
1957年,南郯乡成立,新河头集镇建成大大小小的乡镇机关,决定建合作旅馆(公私合营)。当时新河头有一家小吃店,党委书记直截了当,认为河头几家小餐馆的老板都是街头华子习惯,于是在全镇招揽了酒楼红锅人才,让陈大红有幸被邀请到新河头合作酒店, 然后退出乡镇建设人民公社,在酒店工作了30年,直到老年退休。
要说当时陈大红的咸水鹅已经很有名了,县委的干部或者外地的客人都去了南门,除了喜欢吃鱼,还喜欢吃陈大红的咸水鹅。那时候没有冰箱,菜不容易摆放,冬天还好,夏天是一顿饭一顿饭,其实陈大红是要杀一只老鹅,按照当时的生意,有时候一天只吃一两桌,吃不下怎么办, 大红师傅会把咸老鹅卖给公社食堂,到公社给县里的干部和记者等,品尝这种美味为他炒作,于是陈氏的咸水老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白马湖水乡闻名遐迩。
不过,这种咸水鹅也是珍贵的,数量少,让人吃得大嘴巴,桌上只能尝到一两块,让想吃,吃得越多越想吃,食客的口感提升, 这就好比我们白马湖的美景,关键是回头客,也就是欢迎您再次来到白马湖。
据说陈大红退休的时候,陈浩还没有认真学习过父亲的咸水老鹅的真功,这与陈浩有些浪漫随便的性格有关,而陈大洪是新河头有名的好人,从来没大话教育儿子。改革开放后,陈浩在新河头开了一家小餐馆,当时他并没有感受到特色菜的重要性,咸鹅招牌也还没有出名。
据说陈大红在去世前一年显得非常着急,差点和儿子变脸,坚持要交出自己收藏的特技。

照片:如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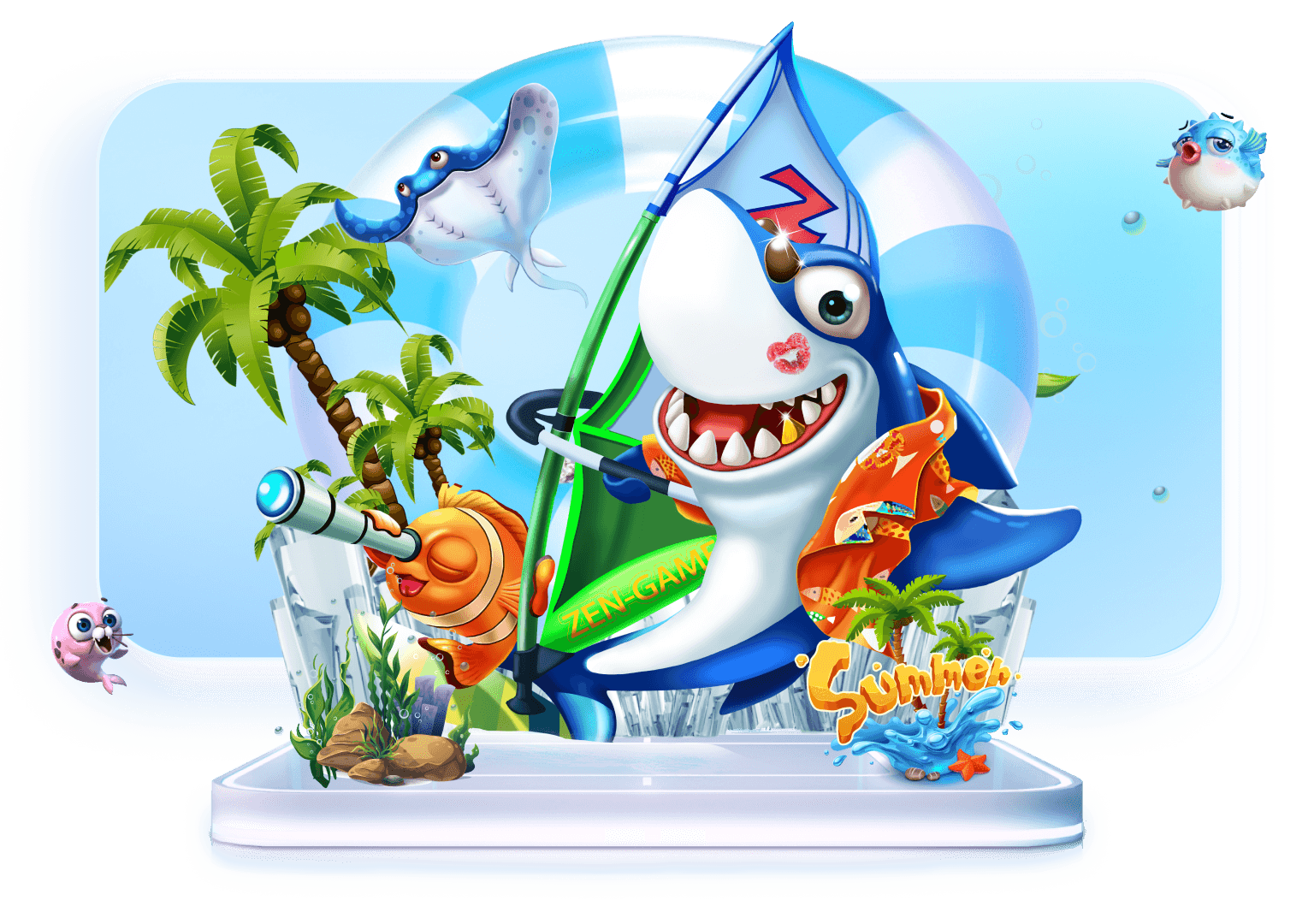
四
而陈浩这一代应该是标准的第三代,也就是说他今天对我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,我只是从他嘴里得到了一些实事求是的东西。
我说你今天能跟我说点特技,让我也写一篇质量更好的纪实通讯,毕竟是为了宣传你,也不想开个咸水老鹅店来抢你的生意。
他说:“我就不瞒你了,有些花样实在是不能随便揭穿,因为现在调皮捣蛋的人很多,还真叫同侪。“我知道,他的邻居本来是镇政府的定点酒楼,和他家的关系一直有些紧张,红锅师傅早就想定手了,但一直没有成功。这位客人只能把自己的现成货端上桌,主人也说不出他那只腌制的老鹅里放的食材和配料,总是那么神秘。
原来是家里人做了咸水鹅,他关上了门门,门口的广告招牌上有电话号码,拿货的客家人大多是先打电话订货的,然后上门取货,还有一些指定的人在暗中交易。他还说,这些闲事都是在晚上做的,工作到很晚就是半天,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人打扰他们。
我知道他跟我说的只是皮毛,像老鹅多半是两岁的鹅,新鹅的嫩骨嫩肉做不出老鹅的味道,老鹅和新鹅他能从鹅毛上辨别出来,一般送鹅到他家的顾客已经知道他的挑剔, 不会欺骗他。还要吃草的草雁,至于吃正大饲料的,他也不想要,十多斤大的雁雁他也不收,雁雁的肉质也不是很好。至于制作他的老鹅的诀窍,比如盐水的浓度,配料的比例,老鹅的热量,还有那些很特别的秘方,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秘方,可能还有一些秘方,也就是说,他自己提到过,父亲临终时送给他的, 当然,他不得不含糊其辞地对付我,你能告诉我这些秘密吗?
不过,他也谈到了这几年镇上的一些尴尬的事情,这些尴尬的事情对他的生意产生了影响,他说秃头夫妇来自宜宾,本来只是做辣鹅的,没想到后来开了个咸水鹅,生意也不错,“夫妻俩有两个摊位,每天还卖几只鹅, 这个方法是不是没学来,我说不出来,说明这只咸水鹅不是我的专利?”
我说:“我很高兴我没有帮你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,如果我写这些材料,人们会认为我在吹。”

五
要说陈浩还是个好人,虽然对我有点警惕,但我总觉得他有一颗善良的心。我经常会开玩笑说,如果我给你写稿子,估计会有人和你竞争你的工作,你为什么不想大展拳脚?
那次,几位老民歌朋友来到台湾和香港,都是老爷子,第一天我就给他打电话,请他准备一桌特色菜。第二天,我和客人在白马湖周围游完后,上岸吃晚饭,去了他家,这确实让我有点不满意。他说:“老哥不会告诉你,楼上最高的客房已经被镇领导订好了,你去明亮的房间吧。”
恰巧那天区的主要领导都来了,他的民歌老朋友也是他的贵客,他们抱怨我为什么忽略了这些贵宾。他有些紧张,说:“你的客人比区里的领导更重要,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我说:“你眼里只有镇上的主要领导人。“今天天气不错,但人家对老鹅的欣赏程度不高,水乡里有几道不值钱的菜,客人们都很欣赏。其实很简单,港台这些老人的生活质量肯定比本地人高很多,就连糖醋萝卜都吃得津津有味,还有小毛虾,宁愿一个个捡起来,却不光顾腌制的老鹅。
我说:“你叫聪明,却被聪明误会了,你当着他们的面这么厉害,这些老头老太太要让他们把仅剩的老大的牙齿扔在这里,你能啃你的老鹅没牙吗?还有你的冷盘,让这些出门的老人不敢碰,让他来回穿梭上厕所,等于是让他去死。再说了,这些老人吃惯了西餐,又没有叉子,还不能吃饭。我说你真的回家了,你能骗你我也骗不了别人。”
说实话,我还给他出了一个主意,“你的名声还是要宣传的,而且你已经快七十岁了,不能把这门功子带进棺材里。目前,信息时代靠包装生存,也可以当大老板,可以批量生产,链式生产,可以请科研人员按照各种生产程序进行机械化生产,还有很多冷冻速冻设备,可以真空包装,保鲜几个月也没关系。”

我这么说的时候,他可能听不进去,但还是能看到他脸上的冷漠。

照片:如悦
六
也许是我戳了戳他的心痛,有那么一刻,就在我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,他似乎想对我说些心痛的话。
“哎呀,哥哥,你哥哥还是没有本事,文化太少,不会握笔,看不清外面的世界。我真的被这只咸水鹅迷住了。这些年外面听过不少名牌、名牌,却一直没有被打动过,外面文盲的人多了,我又算得上是小本事吗?其实,文盲真的是多了盲目的苦,要说老爹留下的秘方,其实全是假的,不是我一步一步发现的,我只知道一个死道理,吃是味道的画面。就这样,八尺两笔就能写一篇文章?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。”
我说:“你怎么知道你在技术上是保守的,不把这个技能教给别人?他说:“这不就是文革时期对私言的批评吗?人家把碗里的一半米饭都吃不饱,到了这个年纪,能吃几块钱就不用跟孩子说话了,口袋里多倒几块钱也不算太热。”
我说:“你可以用自己的本事做个小产业,我们到外面去逛逛,人家卖那个地方的土特产,你说咱们白马湖旅游发达了,外地的游客也多了,每人带走一小袋你,该多少钱?
他说:“我的心没那么高,只是小小的敲门声,只是每天一顿辛苦的饭菜。我说:“你为什么不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呢?他笑道:“还传给我儿子吗?不被儿子骂是件好事。我儿子在上海,不知道是干嘛的,抽烟其实是100块钱一包烟,请桌客人几千块钱,每只鹅20块钱、30块钱他满意吗?他说什么狗屁老鹅,十天的苦都不够我花一天。你要我把这门手艺传给别人,那我就不姓陈了,这是我老父亲在世上说的忌讳。如果要说几年都做不了这份工作,那我就得吃苦了。儿子再有钱,他也不用我,我也不靠他,天天看麻将都值得,来不来也难,不来就停下来捧个小茶壶,天天讲点老活,这才叫享受青福。”
原来他的境界这么高,难怪他不习惯我,我的话似乎惹不起他,脑子里根本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印象。这时,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他家门口,“客人,”他客气地说,“哥哥在这里吃饭,哥哥陪你喝两杯。我说:“谢谢你,我要写你独特的作品,很多人都在关注它。起身告别,他说:“慢慢走。“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,我不做灯泡,回到家后,我花了半天时间才写出这个八卦。
——5月11日写于白马湖畔


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员单位
淮安市民协会副秘书长



